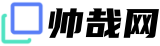谈及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李城不假思索地讲起2017年那个漫长燥热的夏天。那年他28岁,第四次参加高考,用近十年奔波忙碌的“半工半读”生活,如愿换得一张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书。
考上央美后,李城给所有亲戚朋友发信息告知喜讯,很快,在外务工多年不回老家的父母与他在老家团聚。那段时间,整个村的人都在谈论他,亲戚们热络地围绕他们一家,其中有曾坚决反对他考学的大伯。
紧接着,数十家媒体蜂拥而至,他从“央美保安”奋斗成为“央美新生”的励志故事以简短报道的形式登上各大新闻网站。
在北京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里,入学前夕的李城谈起未来设想:“要成为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傲。”而在另一段采访中,他透露“往后还要考北大的博士”。接受东方卫视采访的视频截图,现在依然是李城的微信头像。
然而,2021年从央美毕业后,李城没有成为大艺术家,他也放弃了继续深造的计划。他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求职过程,如今在四川东南边缘一座小城做了私立学校的教务老师。
为了尽快还上读书期间欠下的网贷,他在正式工作、周末兼职之余,还见缝插针地利用碎片时间送外卖。由于负债,他的银行卡已被冻结。
他还保持着大学时寒暑假旅行的习惯,只是从自驾变成了现在的“苦行僧式”的摩托旅行——电摩上绑一张折叠床,骑到天黑就随便找一处路边的角落入睡,没有被子,只有厚一点的衣服盖在身上,下雨被淋湿,就等风干后再盖。如此艰苦的旅行,他视为平庸日常里“几乎是唯一的快乐”。
但我问到“是否满意现在的生活”时,“非常满意”,他脱口答道。
“那些宏大的愿望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李城说,“过去我并不真正了解艺术家究竟是什么样,但在央美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自己不是那块料。或许现在这种生活才是适合我的,因为它不要求我什么。”
读出一个名堂
李城的老家在湖南省衡山县,他对画画的向往,多少受了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个裁缝,李城觉得她是有艺术天分的,她只读过两年小学,却可以无师自通地对着音乐书上的谱子唱出歌,有时随手画些身边的物件,看上去也有模有样。母亲以家里的半截墙做黑板,以裁缝的画粉做笔,一遍遍地教刚学会说话的李城画西瓜,画香蕉,画苹果。一颗种子就此埋下。
小升初的暑假,李城取得父母许可,开始系统地学素描。当时,老师曾借给他一本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书中米开朗基罗从并不富裕的家庭中走出,青年时代便凭实力博得盛名,最终成为艺术巨匠的精彩人生,让李城既羡慕又崇拜。
书的结尾,作者以米开朗基罗的口吻如此写道:“时代造就了我,而我也为时代做出了贡献。”在此后的二十年里,这句话不时在李城心中乍然回响。
2005年,李城作为美术专业生,考进市重点高中衡山四中。高中三年,他大部分时间泡在画室里,偶尔画到忘我,不经意间就是一个通宵。暑假时还会专程前往长沙,去更有名的画室短训。可他对文化课提不起劲,除了画画,其他时间花在了看闲书,打游戏上,有时兴致起了,还会动笔写几首小诗。从高一期末开始,他的文化课成绩排名一直处于垫底位置。
高考结束后,在明知专业课成绩、文化课成绩均不达标的情况下,李城依然在志愿表上填了央美,“要去最好的学校,读出一个名堂,否则不如不去。”
毫无悬念,他落榜了。此后,他开始了边打零工边复读的漫长考学路。
34岁的李城,用性格解释他18岁的挫败,“专注力不够,总是轻易在热衷之事上竭尽所能,无法强迫自己投入枯燥无趣的任务”。
从2008年到2017年,李城辗转于湖南、广东、浙江、北京,做过私立学校助教,保安、流水线工人,空调维修学徒,送餐员……
与百度百科及许多报道中“当了十年保安”的叙述不同,李城在央美的保安生涯前后不过两三年。2012年6月,他来到北京,想参观央美校园。到了校门口,却意外地被保安大哥叫住,问他“要不要找工作”。

这份被他欣然接受的央美保安工作,五年后,成为了他身上最广为人知的标签。在此期间,他因分心复读、学画、参加考试等,在保安大队“三进三出”,每次都待不了多久。他在打工者和复读生的身份之间频繁切换,做过的工作和待过的画室都多得快记不全。
10年间,他参加过四次高考,目标都是中央美院。第一次专业课成绩不理想,第二次、第三次败于文化课成绩。第四次,他以专业课全国第八名,文化课高出录取线一分的成绩,被中央美院录取。
一个现实主义者
被镜头和赞美环绕的状态从夏天一直持续到秋天。9月,刚结束新生军训的李城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一档综艺节目《开门大吉》。

节目中,28岁的他圆脸寸头,戴无框眼镜,穿一件红色运动衫,笑起来拘谨而腼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他顺着主持人的玩笑,在舞台上老实地走起正步,去到指定位置玩猜歌游戏,最终顺利猜出了显然别有深意的四首歌名:《隐形的翅膀》《曾经的你》《执着》和《像梦一样自由》。他的奋斗故事被穿插在几轮游戏间,被主持人深情地讲述。
在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李城都以一个为艺术梦想百折不挠的“努力家”和“梦想家”的形象出现。如果使用大众更喜欢的煽情比喻,他是一个在为六便士奔忙的现实里始终望着月亮的人。这些动人的叙事固然也呈现出部分的真实,但还远远不能构成故事的全貌。
比如,李城并不认为自己应当被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相反,他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人”——选择做美术生,不止是出于纯粹的喜爱,还因为画画是他从小唯一的优势,是他最有可能取得成就的领域。坚持报考央美,也不止是出于对顶尖艺术高校的向往,还因为它“文化课要求不高,专业课如果针对性地学,难度其实也不大。”
“你到底是喜欢画画,还是以画画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我问李城。
“一半一半”,他说。
高考前,北京一家画室听说了李城考学的事迹,邀请他去学习过一段时间,感念于当时的关照,考上大学后,他答应了这家画室老板的兼职邀请。
最初,他只是利用少量课余时间带学生,给自己赚一些生活补贴。但渐渐地,他在画室投入的心思越来越多,甚至专程邀请一批专业水平更高的央美同学去画室教课。这一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他迫切地想在画室教出成绩,为自己打开出路,另一方面,意料之外的高额收入是更直接的诱惑。

媒体报道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画室的积极宣传,更是转化为前所未有的赚钱机遇——冲着他的名气来上课的学生不少,甚至有学生专程从外地进京请他指导,这让他的收入变得相当可观,每年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这个数字已足够让他无法自控地沉入对财富的追逐和对生活的乐观里。过去的九年,李城四处打工却只能赚得微薄收入勉强维生,奔忙的青春里积累了太多疲惫与压抑,而在他成长的家庭中,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民,中年又做农民工”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在向他展示着生活的不易。
“赚钱”这件在他的认知和回忆里都难之又难的事,如今却使他感到,竟可以如此的轻而易举。
大三那年,疫情突如其来,画室收入没了,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不加节制的消费习惯却都还在。为了继续购买昂贵的画材和支付自驾旅行的花销,他开始在支付宝上借钱。随着借还次数增多,网络平台给的额度越来越高,他也抱着“反正找到工作很快就能还上”的心理,无节制地借款。最终,他的债务达到30多万。
李城对未来的乐观预判,源于前几届校友的就业状态。他发现,往届同学几乎都能找到酬劳丰厚的工作,有个熟识的学长甚至在毕业第一年就挣了七十万,“就算我挣不了七十万,那五十万总行吧。”
于是,他放任了自己高涨的消费欲,为旅行采风买了辆旧车;花6000多元买了老师提到的珍贵画册,到手只翻过寥寥几次;毛笔砚台墨块等都要买单价数千元级别的,而且买了很多品种,因为太贵,他存在手里又舍不得用,在毕业前夕全送了朋友。

大学期间,李城为书籍和画材,花掉了近二十万。不过,即便是在“最有钱”的时候,他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都很节俭。
搁浅的梦想
再次出现在央视,李城已临近大学毕业。依然是挑战综艺,也依然是由主持人介绍他“保安变学生”的故事。不一样的是,他的挑战失败了。
这档节目要求选手在100秒内用才艺征服现场观众,李城选择了画自己的电动摩托车,但他没能画完,被观众以反对票提前终结了挑战。主持人委婉地评价:“你画的和观众期待你画出的样子有区别。”李城没有接话。
主持人问他:“同学都比你年纪小,上课有压力吗?”
30岁的李城不好意思地笑,说:“是啊,他们都比我小十岁,还个个比我画得好。我是总被老师批评的那一个。”
这些“被批评”的经历被他诚实地写进了自传里。在他简短潦草且未能完成的一篇自传中,涉及大学生活的章节总共不过千字,却提到了多次被专业课老师否定的回忆。“树石法课,丘老师说我是墨盲”,“素描人体课,廖老师说我形不准”,“线描临摹课,唐老师说我线不好”,“线描写生课,张老师说我比例不准”, “宋画临摹课,姚老师说我基础差,不懂笔法”……
入学前,李城因专业排名高,对自己的绘画水平原本颇有信心,但现实很快迫使他醒悟,原来专业考试和大学学习完全是两码事,和真正的艺术创作更不可一概而论。
除了发现自己基本功不行,水平很难提升外,更令他沮丧的是,在许多次实际创作中,他都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上的匮乏,在他看来,并非由虚无缥缈的“天赋”决定,而是由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搞艺术需要‘脑洞大开’,”他解释说,“但我没有脑洞,因为我没有勇气去创造。”
“孤僻”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另一个概括。他在大学里跟同学关系不好,只有一个“也不爱跟其他人说话的人”做了他唯一的朋友。六人间宿舍里,李城与室友像平行线似的,没有交集地相处。聊不到一起,也玩不到一起,年龄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在他们之间划出了看不见的鸿沟。同学聚餐很少邀请他参加,有时邀请了,他也不愿意去。更不必说那些所谓“艺术家圈子”的活动,许多人争先恐后,而他总避之不及,以至于后来当他想加入书法家协会时,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肯推荐他的人。
学业进展的不顺使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从事艺术创作的才能,而人际关系不佳则使他进一步明白,他也没有混迹艺术圈的交际手腕。曾经他看见有同学画了作品拿出去卖,他也想要尝试,但他画画的速度比别人慢上许多,完成一幅作品需要耗费很多心血,或许是因为“年龄大了”,他常常觉得心力和体力都跟不上,而且画完以后,他的作品往往也得不到期待中的认可,于是他渐渐就不再画了。
成为职业艺术家的愿望搁浅后,他把期待放在了画室上,希望以此实现自己最初也最根本的宏愿:要改变现状,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
入学前,李城在采访视频里骄傲谈起的那个“成为顶尖艺术家”的梦想,不知何时变成了一片轻薄的影子,在灼人的现实里终究失去了它的容身之地。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一种局限性。我问他,“有没有觉得成长环境、视野和心态,影响了你的选择和发展”,他说“没有”。
“活着,就行”
李城在2021年夏天毕业。他所在的中国画专业共有8名毕业生,除他以外,其他人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在本校继续读研。
读书期间,他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了兼职赚钱上,耽误了学业,他的专业水平和文化成绩都“拿不出手”,最后的毕业创作更是不尽人意,差点儿没能毕业。他的经济挑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考研,他要尽快找到工作,偿还本科期间留下的负债。
他打算找一份美术教育类工作,为此还考了教师资格证。但即便有教资,更有一张好不容易拿到的央美文凭,重回社会的李城发现,找工作的难度竟完全超出了想象。
在疫情和政策的双重打击下,他原本计划的就业方向——培训行业一蹶不振,求职机会骤减。北京和老家的工作他都找过,全部落空后,他不得不放弃对地区的要求,托全国各地的朋友介绍工作,仍旧毫无进展。
有一次,他差点儿签了一家深圳的学校,那里的领导和他是校友,两人相谈甚欢,但在最后的面试中,考官让他当场画一幅画,在那以后,学校方面就再也没了消息。李城无奈地想,大概是他画得不好。
再去反省自身,他愈发意识到自己的种种劣势。比如,虽然在很多培训机构工作过,但他直接从事教学的经历并不丰富,而且擅长内容单一,几乎只针对央美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但教学要求的内容是综合性的,大多数学生需要学的恰好是他最不擅长的联考风格。
走投无路时,他只得去做日结工。比如一天160块钱的快递分拣员,以及医疗器材公司的核酸检测采样员。后者的薪酬远没有传闻中高,也不过是一天百元,工作强度却很大。在密密麻麻没有尽头的人群最前端,他穿着包裹全身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因闷热和口罩而呼吸困难,橡胶手套戴得太久,指尖也被汗水浸泡得微微发痒。
“生活很现实,但只要活着就行了。”李城想。顾不上什么名校包袱,他领到好不容易挣来的“辛苦钱”,久违地感到开心。这种随时都能赚到钱的感觉,重新带给他一种踏实的快乐。

毕业半年后,一个同学联系他,说兰州老家的哥哥开了一所培训机构,可以让他去上课,只是工资不高,一个月四千。李城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准备接受,但母亲却没有这么果断。她为他感到可惜,迟疑着问:“你就不嫌工资低?”李城想了想,说:“那也没办法啊。”
结果他没去兰州。临行前,他得到了一份在深圳教小孩子画画的工作,月薪六千,于是他选择了去深圳。一个月后,又有另一个机会找到他,一所知名连锁学校请他去山东做“总监”,承诺每个月给1万2千元。奔着这份翻倍的工资,李城马不停蹄地赶往山东。去之前,父母出于一种朴素的危机意识,劝他“当心一场空”,李城不以为意,可结果偏偏让他们说中——入职半个月,他意识到校方在想方设法拖延,不肯给合同,也不肯在合同上盖章。眼看情况不对,他选择了尽快离开。没过多久,当时的同事告诉他“学校解散了”,他们曾试图苦苦支撑,疫情下最终还是没能幸存。
2022年7月,在毕业一整年后,李城终于得到了一份令他满意的工作——四川泸州一所私立高中的教师。工作是同学介绍的,李城坦诚地说:“靠我自己,那是肯定找不到。”
现在,他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学校的教务,具体来说,就是负责给学生点名、联系家长、组织学生大扫除等。他不用带高考生,只带高一高二,甚至不用教学生们画画,只负责监督他们按时来校。虽然专业能力没了用武之地,但他心里清楚,学校要的也不是他的专业能力,不过是用他一张文凭作招牌,哪里谈得上什么“浪费”。
除本职工作外,他还带了几个周末学书法的小徒弟,偶尔也去上几堂酬劳很低的公益课,或是在培训班上四五十个学生的大班课,以及上门当美术家教。实在没有活干,他就在闲暇时送外卖,一小时能赚大约二十块钱。
前几年所欠的三十多万网贷因逾期未还,如今加上罚息已经达到六十多万,他的银行卡也因此被冻结,学校的工资到了卡上却不能花,只能靠业余挣的钱勉强生活。在工作逐渐稳定后,他决心用接下来的几年把欠款还清。
顺利的话,他想在这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但过往的漂泊不定使他很难对未来的安稳有足够的信心,总有觉得“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他想,如果哪天学校不再需要他,就会立刻把他开掉。但他又乐观地安慰自己:万一私立学校干不下去了,就去开兴趣班,一样可以过得好。
他也后悔大学四年在学业上的荒废,“如果专业课学好了,应该可以读研,读研了就可以和同学一样去深圳的学校当老师”。
到了寒暑假,李城会骑上一辆电动摩托车,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旅行。巧的是,在过去那场以“挑战失败”告终的节目里,他画的就是这台小电摩。当时他解释了画它的缘由:正在考驾照,以后就能开上汽车,不会再开摩托了。后来,他也确实开着他的红色小面包车几乎跑遍全国,但现在,因为开不起每公里要花一块钱的汽车,他再次骑上陪伴他多年的小电摩。

车上载了一台发电机、一个十升的油桶,一些极其简单的生活用品,以及一张简易折叠床。摩托能载的东西实在有限,他带不了被子,因此当夜里露宿郊野,他会将一些稍微厚实的衣服当成被子来盖,但刮风的时候还是冷,偶尔被突如其来的雨连人带衣一起淋湿,便只能静静等雨停了,让风把衣服自然吹干。简单的洗漱他会在路过加油站时完成,但洗澡就毫无办法,只能忍耐到回家。这样艰苦的旅行在常人眼里几乎和“快乐”毫无关系,但李城有一套他的逻辑:这是一种人为的艰苦,而人为的艰苦都是快乐的。
李城画画的时间少了,除了教学生的时候自己也画一下,其他时间总是不想动笔。他想起有个大学美术老师曾说,最讨厌的就是画画,因为画画变成了工作。李城想,他现在或许也是这样。以前一直觉得画画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现在却不再是乐趣了。
他有了新的想法和目标:年轻时多攒些钱,今后回到老家,参照城里的老年大学,建立一所以招收农村老人为主的“长辈学堂”,让老人们一起画画、写书法、唱歌跳舞,其乐融融。
李城目睹过外公、奶奶生命最后几年的状态,孤独、衰老和死亡贯穿在老人的生活当中——外公的老友陆续离世,再无人陪他打扑克,奶奶摔了一跤从此走不了路,生命困于病床和轮椅之间。旅行途中,他也见过太多农村无人陪伴的白发老人,他觉得他们最后都是“孤单死的”。
但大学里的老教授就不一样,他们“越老越热闹,多得是朋友”。李城打算亲自教会父母写字画画,让他们持续学习新知识,还要安排他们给孙辈开讲座,享受大学教授那种传道授业的快乐。
2023年7月,李城骑着小电摩去了趟云南。月底从泸州出发,经过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和大理等地,12天后回到泸州。

其实在最初,他想去的是腾冲,但走着走着,又觉得去哪里都无所谓。
出发第一天,他路过宜宾,想起以前一起玩玉雕的朋友住在附近,打了个电话。对方正和朋友吃饭,热情地喊他参加。几个人边吃边聊,没想到其中恰有一个他所在高中的学生家长。
李城问,孩子成绩怎么样?
家长说,一般吧,985肯定考不上,211或许还有希望。
李城说,那你让他学美术吧,咱们可以冲清华美院。
内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李城提供